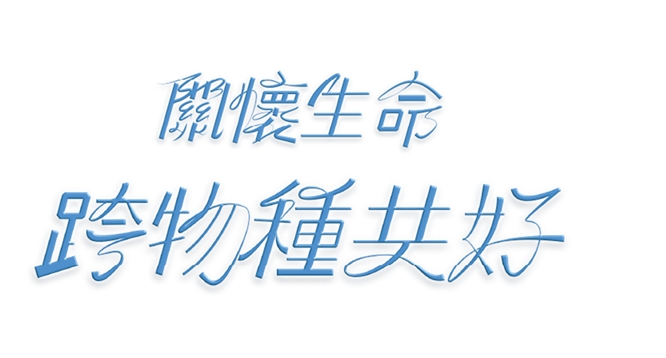
在當代動物倫理學、環境倫理與社會政治的發展中,「跨物種共好」(multispecies flourishing,或譯為多物種共好)作為一項新興論述,逐漸被提出以回應既有理論框架在面對現實挑戰時的侷限性。
傳統的動物保護行動,往往依賴人類對特定物種的情感與道德關懷作為行動動機,導致其關注對象侷限於與人類較親近或外表吸引的動物,例如伴侶動物或具有象徵意義的「旗艦物種」。這種做法容易忽視其他物種的處境,形成倫理考量上的偏誤。
動物福利理論則試圖以科學方法衡量動物的痛苦與舒適程度,進一步提出改善飼養、運輸、屠宰等實務,但其政策實踐經常受限於產業利益的妥協與行政可行性,難以真正挑戰動物被系統性剝削的結構。
動物權理論則主張動物應享有與人類相似的道德地位,甚至法律上的基本權利,然而其架構多以人權為類比基礎,在面對語言能力、自主意志等難以直接移植至非人動物的特質時,往往無法涵蓋所有動物的倫理與政治需求。
因此,「跨物種共好」應運而生,試圖跳脫以人類道德能力為他者得救前提的倫理模式,主張每一種生命型態皆在其生態位中具有內在價值與意義。透過這樣的概念,我們得以重新反思:人類如何透過制度安排、科技發展與資源分配影響他者(動物)的生存條件?又該如何重新定義「共存」與「繁榮」的倫理與政治基礎?
關懷生命協會的「跨物種共好」論述將以三大支柱——「反省物化動物」、「健康一體」、「法制主體性」作為核心架構,重新建構人與非人動物關係的倫理與政治路徑,期望挑戰人類中心主義,並在觀念反思、國際網絡與政策實踐三層面,建立一套具實用主義精神的跨物種共好的藍圖。
一、觀念反思:反省物化動物
動物不應只是被交易、剝削的資產,而應是擁有內在價值的行動主體。因此,動物並非商品,也不是任人宰制的客體,而是嵌入於社會與生態網絡中的個體,具有表達、互動與回應的能力。
此觀點回應了傳統動物保護思維的侷限。過去動保行動往往仰賴人類對動物的情感與道德關懷,但這導致關注對象侷限於與人類較親近或外表吸引的物種,例如伴侶動物或「旗艦動物」。主體觀則要求我們跳脫這種情感選擇的偏誤,將動物視為不可替代的主體,無論其是否與人類相似,而我們無論「愛不愛」牠,都應該重新思考量他的倫理地位。
這一觀點在推動保育與動物保護教育中尤為關鍵。也是關懷生命協會長期在動保教育的努力目標。
在108課綱「共好」理念的推動下,我們認為,倡議應以「尊重」、「關懷」、「正義」三大品格作為教育核心,引導學生反思動物在社會中的定位,培養以非商品化的視角理解生命。這三大品格並非獨立,而是彼此聯繫、相互支持,共同構成了實現「跨物種共好」不可或缺的倫理基石。
「尊重」是我們反思物化動物、肯定其主體性的重要源頭,也是倫理思考的基石。**它要求我們超越人類中心的視角,去認識並承認每種動物獨特的生命形式與內在價值。瑪莎・納斯邦(Nussbaum, 2006)的「能力取徑」(Capabilities Approach)為此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支持。納斯邦主張,動物不僅能感受痛苦,更擁有表達情感、建立關係、探索環境等多元能力。因此,真正的尊重,在於積極保障動物有機會實現其天賦潛能,讓牠們能以其物種特有的方式去生活與繁盛(flourish),而不僅僅是消極地避免痛苦或虐待。這種以「促進每一物種實現牠們核心能力」的倫理觀,挑戰了將動物視為被動承受者的物化觀點。
「關懷」是反省物化動物的另一重要源頭,也是連結我們與動物之間情感和認知的橋樑。卡羅・吉利根(Gilligan, 1982)與奈爾・諾丁斯(Noddings)所發展的關係倫理學,反對將道德簡化為抽象原則,轉而強調具體情境中的關係、照顧與責任。此倫理學派主張,我們與動物之間的倫理義務,許多時候源於實際的互動與相互依存關係。因此,教育應鼓勵學生傾聽動物在特定脈絡中的「聲音」(即便那不是人類的語言),學習以同理心與情感投入的方式去理解並回應牠們的需求,辨識動物在特定處境下的苦樂。這種具體的、關係性的理解,使我們能更深刻地體認到動物作為個體的存在,而非冰冷的「物」。
「正義」是反省並拆解物化動物的關鍵力量,也是保障動物福祉的社會實踐。彼得・辛格(Singer, 1975)以效益主義為基礎,主張所有能感受痛苦的個體,其利益應被平等考量,挑戰了物種歧視的合理性。湯姆・雷根(Regan, 1983)則進一步主張,某些動物因具備「生命主體性」(subject-of-a-life),應享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不應淪為人類利益的工具。這兩者的理論,共同為動物爭取了非物化的道德地位,要求我們在制度上賦予牠們不容忽視的聲音。而納斯邦的「能力取徑」在此基礎上,更將動物議題提升至政治哲學的「正義」層次。她認為,當社會制度系統性地剝奪或阻礙動物實現其核心能力時,就構成了對動物的「不正義」(injustice)。因此,保障動物福祉、為其創造得以繁盛的條件,並非僅是個人慈善或選擇,而是社會無可迴避的集體責任與正義要求。這種以「正義」為導向的思考,促使我們檢視並改革那些將動物工具化、商品化的社會結構。
這三種倫理思考——肯定動物的內在價值與潛能、關懷其在關係中的具體需求、並追求保障其權益與福祉的社會正義——讓我們得以深刻反省過往對於動物的物化,凝聚未來推動保護的方向,使「跨物種共好」從理念走向可實踐的社會藍圖。
二、國際趨勢:健康一體
在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等動物倫理學者的影響下,現代社會已逐步接受以「動物是否能感知痛苦」作為倫理考量的重要依據。然而正如 Goetschel (2022)指出,若僅停留於倫理層面,而缺乏法律或制度化的保障,則難以有效推動結構性的改變。因此,「跨物種共好」作為一種新型政治訴求,應與「健康一體」(One Health)、「福祉一體」(One Welfare)等國際政策倡議接軌,將動物福祉與人類健康、環境永續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健康一體」原先由獸醫學界提出,強調人類、動物與環境健康三者間的密切關聯,已被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等國際機構納入重要的政策方向。這一觀點認為,傳染病的預防、食物安全與氣候變遷的因應,不能僅由人類醫療體系單獨處理,而必須透過跨領域、跨物種的協作來達成。
例如在食品生產體系中,工業化畜牧業為追求效率與利潤,導致動物被長期困於狹小空間,極易滋生疾病並促使抗生素大量使用,進而加劇抗藥性問題。除了侵害動物福祉外,也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風險;而相關排放與廢棄物管理不善,更對水資源與空氣品質造成長期污染,顯現人與動物比想像中的密不可分。
在城市規劃中,都市擴張與基礎建設常以犧牲自然棲地為代價,使野生動物棲息空間急劇萎縮,加重人與動物之間的衝突風險,如車禍、食物競爭與疾病傳播等,也因此成為城市永續治理的重要挑戰。「跨物種共好」在此脈絡下強調,動物不應僅被視為風險來源或管理對象,而應納入政策評估與規劃過程,與人類一同考量,獲得必要的生存條件、健康保障及福祉。
因此,從傳染病防治到面對氣候變遷、從農業轉型到城市設計,「健康一體」能作為一個實際在政策上參考的策略,協助我們建構一個對所有生命更具包容力的制度與架構。
跨物種共好的實踐不只是價值觀,也必須成為全球公共政策與國際合作的起點,因為動物早已是人類社會、環境與健康議題交匯處的重要參與者。尤其當今世界面臨新興傳染病、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等系統性挑戰,我們更需從跨物種的角度重新思考健康與永續的定義。
在此背景下,「一體健康」(One Health)與「一體福祉」(One Welfare)這兩項國際倡議提供了強有力的架構。它們打破傳統人類中心的醫療與福祉觀點,主張人類、動物與環境健康彼此交織、不可分割。動物是健康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其角色與處境對整體社會結構具有高度影響力,牠們的處境將直接反映與影響整體社會的穩定與韌性。
這樣的思維轉向實踐了「網絡中的個體」的倫理觀點,使我們得以將動物視為關係中的行動者,從而重新界定其在健康與社會系統中的角色。這項轉變有助於改善動物福祉,並為跨領域、跨物種的合作制度提供可行的政策方向與倫理基礎。
相信這樣的策略,將來會是有志於動物保護工作者從事科學調查與研究的起點,研究,將不只是監測、數據蒐集等知識生產工作,更應該是讓動物在政策設計中「被看見」的過程。當然,這也會是關懷生命協會未來努力的方向。
三、國內政治:法制中的主體性
最後,若「跨物種共好」要真正落實,還必須使動物在法律中擁有可被承認與代表的主體性。
在唐納森與金利卡(Donaldson & Kymlicka, 2011)所提出的「動物公民」理論中,動物應依與人類社會的互動關係,區分為三種政治地位:
首先是「公民」(co-citizens),指的是與人類建立長期依賴關係的馴化動物,如伴侶動物與農場動物。這些動物在日常生活中與人類共同生活,應享有居住安全、醫療照護、參與機會等社會權利,並被納入共同治理的架構中。
第二是「共居居民」(denizens),主要指的是在城市、人類社會邊緣地帶活動的動物,如流浪貓狗或城市中的鳥類與小型哺乳動物。這些動物雖非人類主動飼養,但已深度參與人類環境中的生存網絡,因此應擁有基本的居留權與不受驅趕、虐待的保障,並能在政策中獲得適當的管理與照顧。
第三是「主權社群」(sovereign communities),即保持野性、自主性並遠離人類生活的野生動物族群,例如山林中的黑熊或海洋中的鯨豚。這些動物應被視為擁有自我治理權的群體,其棲地應受到尊重,不受人類干預、驅趕與侵擾。
這套分類不僅為動物如何在政治社群中被承認、被代表提供了清晰架構,也跳脫了以往僅以人類情感或生物特徵作為判準的保護邏輯。它使我們得以真正將動物納入法制與民主制度的討論之中,視為應被考量、協商與保障的政治主體。
最近台灣蠻野生態心足生態協會獲得為白海豚提出公益訴訟的代表權利,正表示司法系統正逐漸接受動物是享有權利的主體,並能由兼具法律專長與動物專業的代理人為之發聲。未來,動物保護或保育團體,可以在立法及政策領域上持續前進,落實動物主權及其代理制度。
實用主義作為橋樑
最後,不論是前述的「反省物化動物」、「健康一體」、「法制主體性」,都必須經過實用主義的考驗。杜威(Dewey, 1922)與詹姆斯(James, 1907)曾強調,真理與倫理的價值不在其抽象邏輯是否完備,而在於其是否能回應實際問題、產生可見的社會效果。實用主義主張「想法的意義在於其後果」,倫理命題不應被視為永恆不變的真理,而應透過實驗與經驗加以驗證。
這樣的哲學精神對於動物保護工作也具有高度啟發性。動物倫理的實踐應從現實脈絡出發,辨識現行制度下動物所處的不正義處境,並透過教育、制度調整、國際合作等多元路徑,推進可觀察的改善。實用主義也提醒我們,改革往往需仰賴不斷的試錯與調整,而非一蹴可幾的道德理想。因此,在推動跨物種共好時,我們應以開放而務實的態度因應不同物種與情境的多樣性。
實用主義亦重視「參與式決策」,民主,不僅是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意味著,在動物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動物保護或保育團體,在參與不同利益關係人的商議中,會持續維持上述論述方向,打造出更具正當性與韌性的制度架構,逐步落實跨物種共好。
結論
因此,無論是在課綱中落實「以尊重、關懷、正義為核心的動物倫理」、在國際協議中納入動物福祉、或是在法制過程中確保動保權利的代表性,每一個實踐現場都需要經歷反覆的檢討、實驗與修正。實用主義敦促我們不斷檢視當下制度對不同物種的戕害,並勇於創新,使社會邁向真正的跨物種共好。
透過反省對動物的物化、健康一體的國際對接與實踐法制中的主體性,我們希望能回應當代的生態與社會危機,重新思考人與非人動物在政治共同體中的位置與關係。
在這條路上,跨物種共好,是我們共同的願景,而實用主義則讓我們持續前行。
參考文獻:
- Dewey, J. (1922).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Donaldson, S., & Kymlicka, W. (2011).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etschel, A. (2022). Animal welfare as the basis of One Health: A UN convention on animal welfare, health, and protection. Animals, 12(13), 1770. https://doi.org/10.1079/cabionehealth.2024.0003Cabinet Digital Library
- James, W. (1907).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Longmans, Green, and Co.
- Nussbaum, M. C.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Belknap Press.
- Regan, T. (1983).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nger, P. (1975). 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Review/Random House.